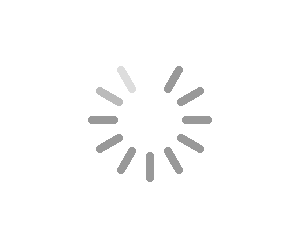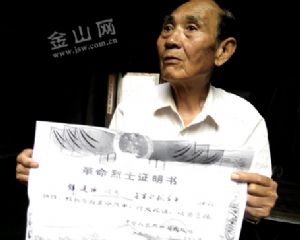来源时间为:2019-11-13
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功用观

文渊阁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源远流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图书馆,不只是藏书和借书的地方,而且是集藏书、育人、资政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同时也是国家文治政策的实施载体。
蒋永福
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藏书以供治学育人的场所,就是图书馆。
清末之前,中国人未尝使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一词,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思想理论却贯穿整个古代时期。是故,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说“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说明先秦时已有国家藏书之所及其职业人员。
在中国古代,一般以殿、阁、楼、馆、府、院等名词指称图书馆,至唐宋始,人们往往用“馆阁”“文馆”“藏书楼”等名称泛指图书馆。本文用“馆阁”一词泛指中国古代的图书馆。
先秦时期的馆阁,一般设于宗庙之中,所谓石室、金匮、盟府是也。西汉初萧何令建的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等,就已具备馆阁功能(用于藏书和学术活动)。东汉的兰台因其兰台令史兼负著述、校书之责而兼具馆阁性质,东观则是完全意义上的馆阁设施。魏晋南北朝至隋代时期皇宫内所建各类殿、馆、阁、观、院等,其中不少亦属馆阁。唐代、五代的“三馆”(史馆和昭文馆、集贤院)以及宋代的“三馆秘阁”,无论在名称上还是在体制上,都已具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馆阁性质,而文渊阁、《四库全书》七阁等就是明、清时期的皇家馆阁主体。
可见,中国古代具有源远流长的馆阁传统,这说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是非常重视馆阁建设的。之所以重视馆阁建设,是因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认识到了馆阁所具有的独特功用价值。
汉唐时期的馆阁功用观
关于馆阁的功用,成书于东汉末曹魏初的《三辅黄图》卷六“阁”条的概括最为精要,即其所云“藏秘书,处贤才”。这一概括是从汉代的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所发挥的功能中概括出来的。从汉代以后的历代馆阁功能看,这一概括极具统摄性和准确性。所谓“藏秘书,处贤才”之馆阁,实际上是一个书与人二合一结构,即指“以书储养人,储养人以治国”为目的的一种文治之器。
说到馆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皇家馆阁大多由帝王令建,所以馆阁实际上是帝王的“治国之器”之一,或者说是帝王专为文人参与治国(文治)而建的“治国之器”之一。建立“治国之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探寻“治国之道”。也就是说,馆阁是帝王的文治之器,而不是用以提高民众文化素养的“群众文化设施”,也不是用来为大众传播文化知识或信息的“大众传播机构”。这就是古代馆阁与近现代图书馆在性质和功用上的最大区别之一。正因为建馆阁以探寻“治国之道”为目的,所以皇家馆阁不仅具有文化功用,而且具有极强的政治功用。
古代中国人就是从文化功用和政治功用两方面认识馆阁之功用的。如《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弘文馆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义轻重,皆参议焉”;集贤殿书院“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可见,馆阁的文化功用主要体现在“详正图籍,教授生徒”。
馆阁的政治功用主要体现在发现、推荐、培育人才,著述撰文,参政议政。时任秦王的李世民在任命“十八学士”的手令《置文馆学士教》中明确指出了设立文馆的目的在于“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宜令并以本官兼文馆学士”。在这里,李世民把文馆的功用定位于“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已经涵盖了文馆的政治功用与文化功用;同时,李世民又把文馆喻为“幕府”,点明了文馆的咨询参谋机构性质。这就是李世民以及唐代早期社会的馆阁功用观,即馆阁为文治之器之一。
不过,我们要知道,把馆阁的功用定位于文治之器,这是一种宏观定位,其内涵和表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如唐中宗景龙年间,弘文馆改名为修文馆,馆职人员主要从事赋诗宴乐之事,诚如中宗所言“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欲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唐诗纪事》卷一《中宗》篇)。这就表明,中宗时期馆阁的主要功用在于文化娱乐,而育人、资政功用大大削弱了。唐玄宗时期着重建设的是集贤殿书院,但建设重点在于大量抄写四部书副本、刊校书籍并编制书目(如编制《群书四部录》二百卷等)、编纂和颁发官修图书等,此外,馆阁学士还承担草诏和侍讲职责。可见,玄宗时期的集贤殿书院的主要功用在于文献资源建设,附带承担其他事务,也就是说,此时的馆阁功用主要表现为文化功用,而政治功用不如唐太宗时期显著。
这种变化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馆阁的功用需求不同以及不同的帝王持有不同的馆阁功用观所致。玄宗在解释把集仙殿改为集贤院的理由时说:“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这里的“其实”,在太宗时期更多地表现为馆阁学士的资政功用上,而玄宗时期则更多地表现为馆阁的文献整理与撰述的“济治之具”功用上。
两宋时期的馆阁功用观
宋代是馆阁建设成就极其辉煌的朝代。在宋代,“治书以育人,育人以文治”的馆阁功用观更加明确和贯穿始终。所以,宋代的历任帝王大多能够明确指出馆阁的资政功用和养育人才功用。
在这方面,宋太宗首先做出了“定调”性导向,如其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以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宋太宗的表率及其“三馆秘阁”建设成就的感召下,其后的帝王亦大多能够继承其馆阁建设指导思想,如宋仁宗曾指出“馆职所以待贤俊……图书之府所以待贤俊而备讨论”;宋英宗曾指出“馆阁所以育隽材”;宋高宗曾指出“仰惟祖宗肇开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兴,而一代致治之原盖出于此。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亲御榜题,肆从望幸之诚,以示右文之意”;宋孝宗曾指出“馆职学官,祖宗设此,储养人材”。
在帝王的倡导下,宋代的文人学者们亦大多把馆阁视为治书育人的文治之器,如宋哲宗元祐年间,右正言刘安世上《论馆职乞依旧召试状》云,“祖宗初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累圣遵业,益加崇奖,处于英俊之地而励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廪食太官,不任吏责,所以成就德器,推择豪杰,名卿贤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无愧前古”;高宗时期的丞相范宗尹等上奏云,“祖宗以来,馆阁之职所以养人才、备任使,一时名公巨卿皆由此涂出……今多难为弭,人才为急……宜量复馆职,以待天下之士”。
馆阁的资政功用,不仅表现在所藏图书能够为统治者提供教化、治乱经验,更为直接的表现是馆职人员的咨询顾问作用。馆职人员之所以能够以咨询顾问方式参政、议政,靠的是其“学士”身份。
我们知道,首次在馆阁中设学士职务的是南朝刘宋政权所置总明观(亦称总明馆)。总明观建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六年(470),设祭酒一人,又设玄、儒、文、史四科学士各十人。“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韩愈说:“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阅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雠官,曰‘学士’,曰‘校理’,常以宠丞相为大学士,其他学士皆达官也。”按照韩愈的说法,校雠官(馆职人员)队伍中的主体人员称为“学士”。宋代也承袭了这一建制传统及其称谓,如程俱在《麟台故事》中所言,“故事,进士唱名日,馆职皆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馆阁官许称学士,载于天圣令文”。也就是说,馆职人员可以以学士身份“备顾问”。在宋代,即使没有“学士”之称的修撰、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等馆职人员,亦有参政、议政的资格。据此,程俱在记载北宋馆职人员的资政情况时云:“祖宗时,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则三馆之士必令预议。如范仲淹议职田状、苏轼议贡举者,即其事也。详议典礼,率令太常礼院与崇文院详定以闻,盖太常礼乐之司,崇文院简册之府,而又国史典章在焉。合群英之议,考古今之宜,则其施于政事典礼,必不诡于经理矣。熙宁中,轼任直史馆,尝诏对,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这就表明,宋代的帝王和臣僚们已充分认识到了馆阁作为简册之府以其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发挥咨询、顾问、议政等资政作用的价值。
馆阁不仅在于文献资源建设(文化功用),还应具有聚集人才以资政的政治功用。对此,范仲淹明确指出:“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
曾巩在论及宋初馆阁的藏书建设和人才建设成就时指出:“三馆之设,盛于开元之世,而衰于唐室之坏……宋兴,太祖急于经营,收天下之地,其于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备也。太宗始度升龙之右,设置于禁中,收旧府图籍与吴蜀之书,分六库以藏之。又重亡书之购,而间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图书始复聚,而缙绅之学彬彬矣。悉择当世聪明魁垒之材,处于其中,食于太官,谓之学士。其义非独使之寻文字、窥笔墨也,盖将以观天下之材,而备大臣之选。此天子所以发德音、留圣意也。”范祖禹在《上哲宗论差道士校黄本道书》中指出,“祖宗置三馆秘阁以待天下贤才,公卿侍从皆由此出,不专为聚书;设校理、校勘之职,亦非专为校书”。
范仲淹、曾巩和范祖禹的言说其实都在阐明这样一种馆阁功用观:设馆阁以治书,治书以养人才,养人才以资政。
明清之际的馆阁功用观
与汉隋唐宋相比,明清之际的馆阁功用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明太祖朱元璋于13